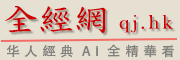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郡人。祖父高泰,事跡在其叔父《高湖傳》中有載。父高韜,少時以英朗知名,同鄉人封懿雅相敬慕。任慕容垂的太尉從事中郎。魏太祖平定中山,任高韜為丞相參軍。早年過世。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為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裏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
高允少年喪父,大器早成,有神奇的氣度,清河人崔玄伯見到他十分驚異,感歎說:“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我隻擔心自己不能親眼見到。”高允十來歲時,為祖父奔喪還歸本郡,家中財產都讓給兩個弟弟而自己身歸沙門,取名法淨。不久又還俗了。高允喜好文學,擔笈負書,千裏求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其愛好《春秋公羊傳》。郡中召他為功曹。
神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征,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征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複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
神..三年(430),魏世祖的舅舅陽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將軍,鎮守鄴城,任命高允為從事中郎,當時他已有四十多歲了。杜超因為春天快到而諸州囚犯多不能判決,於是上表讓高允與中郎呂熙等人分頭前往各州,共同評決獄事。呂熙等人都因貪汙枉法獲罪,惟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賞。杜超幕府解散之後,高允回家教書,受其學業的有一千多人。神..四年(431),他與盧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為中書博士。遷任侍郎,與太原張偉二人都以本官兼任衛大將軍、安樂王元範從事中郎。元範,是魏世祖的寵弟,西鎮長安,高允輔佐他很得當,秦地人很是稱讚他。不久高允就被征召還朝了。高允曾經作《塞上翁詩》,詩有混同高興悲傷、遺落得失的情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元丕西討上絡,高允又以本官參與元丕軍事。記在《元丕傳》中。涼州平定後,因參與謀劃之功,朝廷賜高允爵汶陽子,加授建武將軍。
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並識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雲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複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鹹怪,唯東宮少傅遊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遊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複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後來帝下詔讓高允與司徒崔浩編撰《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當時崔浩召集眾多術士,考校漢代以來的日月薄蝕、五星行度,並識別前史的誤失,另撰魏曆,拿給高允看。高允說:“天文曆數不可憑空而論。大凡善言遠古的必定驗於近世。況且漢代元年(前206)冬十月份,五星聚於東井,這本是曆術之淺。而今譏諷漢史,而不覺得這是錯誤的,恐怕後人譏今就像今天我們譏古一樣,鬧出笑話。”崔浩說:“你所說的謬妄指的是什麼?”高允說:“我查《星傳》,金水兩星常常附日而行。冬季十月,太陽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卻出於寅北。這兩星是什麼原因背日而行?這乃是史官想神化漢高祖受命之事,不再推之於理的結果。”崔浩說:“想要變化什麼地方不行,你獨不懷疑三星之聚,卻怪二星之來,是什麼道理?”高允說:“這不能夠空言相爭,應加審查才行。”當時在座的人都很奇怪,隻有東宮少傅遊雅說:“高君擅長曆數,應當不虛妄。”過了一年多,崔浩對高允說:“先前你所說的,不能使我心服口服,等到我重新考察一番,果然如你所說,五星以前三月聚於東井,而不是在十月份。”又對遊雅說:“高允之術,猶如陽元的射箭技藝。”眾人全都感歎佩服他。高允雖然精於曆數,當初卻藏之於懷,也不論說,隻有遊雅屢屢以災異求教於他。高允說:“過去的人說,知之甚難,既已知道又怕泄漏,所以知道不如不知道。天下奇妙的道理甚多,為什麼偏偏要問這個。”遊雅於是作罷。
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眾。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雲:方一裏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裏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鬥,不勤則畝損三鬥。方百裏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複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不久高允以本官任秦王元翰師傅。後又命他教授魏恭宗經書,受到了很好的禮遇。帝又詔高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一同議定律令。魏世祖召高允一起討論刑政,高允的言論很得世宗賞識。帝問高允說:“政事千頭萬緒,什麼是第一位的?”當時,魏朝多禁封良田,又京城中遊民很多。高允因此說:“臣少時微賤,所了解的隻有田耕之事,請讓臣說一說農事。古人說:一裏方圓的範圍可以辟田三頃七十畝,百裏方圓則有田三萬七千頃。如果農人勤耕,則每畝可增糧三鬥,不勤則損失三鬥。方圓百裏增加減少的數量,合計有糧二百二十二萬斛,何況天下如此之廣呢?如若公私都有糧食儲備,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什麼可憂慮的呢?”世祖很欣賞他的說法。於是廢除田禁,全部把它們交給老百姓。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並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
當初,崔浩推薦冀、定、相、幽、並五州之士數十人,每人都當郡守。恭宗對崔浩說:“先召的人,也是州郡官職的人選,在職已久,勤勞政事未見酬答。現今可先補前番征召的人為郡縣守令,以新召的人代為郎吏。而且太守縣令治理百姓,應該派那些有經驗的人。”崔浩堅決不讓步,固執地派了那些新征召的人。高允聽說此事,對東宮博士管恬說:“崔公要遭殃了!堅持自己的錯誤,而要與皇上爭個高低,這哪會有什麼好結果。”
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並州,受布千匹,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為首為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鹹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為親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對,竟為世祖所疏,終獲罪戮。
遼東公翟黑子得到魏世祖的寵信,出使並州,得到了千匹絹帛的賄賂,不久事發。黑子討教於高允說:“主上問我,是彙報真實情況還是說假話?”高允說:“公是皇上寵臣,回答時可據實以報,你又可自表忠誠,必然會沒什麼事的。”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人都說自首後罪不可測,應該說假話。黑子以崔覽等人為知己,反而對高允發脾氣說:“你的說法,是引誘我去死,那太不值得了!”於是與高允斷交。黑子在皇帝麵前說了假話,終被世祖疏遠,最終獲罪被殺。
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郤扌剽性巧佞,為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並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貧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
當時,著作令史閔湛、郤..性情奸巧邪佞,被崔浩所信任。見到崔浩所注釋的《詩》、《論語》、《尚書》、《易》,便上疏,說馬、鄭、王、賈雖然注述《六經》,都多有疏漏謬妄,不如崔浩的精到細微。請求皇帝收集國內諸書,藏於秘書府中。頒發崔浩所注述的,命天下學子學習。並請求皇帝下詔讓崔浩注釋《禮傳》,讓後生能夠看到精正的經義。崔浩也上表推薦說閔湛有著述的才能。接著閔湛等勸崔浩刊印自己所撰的國史,以圖不朽,想要彰明崔浩執筆之績。高允聽說,對著作郎宗欽說:“閔湛的所作所為,一不小心,我擔心它日後會成為崔門的萬世災禍。這樣我們這些曾經參與其事的人都要大禍臨頭了。”不久,災難就降臨了。
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製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雲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敕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當初,崔浩被收捕,高允在中書省值班。恭宗讓東宮侍郎吳延召來高允,讓他留宿宮內。第二天,恭宗入廷奏啟魏世祖,命高允隨行。到宮門前,恭宗對高允說:“進去見皇上,我隨你去。假如皇上有什麼話問你,你就依我告訴你的應答。”高允說:“這是為的什麼事呢?”恭宗說:“進去你就知道了。”就進去見皇帝。恭宗說:“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中,臣與他相處多年,高允小心謹慎,臣很了解他。高允雖然與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賤,隻有聽命於崔浩。臣請求寬恕他的性命。”世祖召見高允,對他說:“《國書》都是崔浩所寫的嗎?”高允回答說:“《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寫。《先帝記》以及《今記》,為臣與崔浩一同寫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隻是總裁修訂而已。至於注疏,為臣所作多於崔浩。”世祖大怒說:“這比崔浩的罪行還嚴重,怎能留給生路!”恭宗說:“天威嚴重,高允是小臣,一時間迷亂失次。臣先前問他,他說都是崔浩寫的。”世祖問:“真像東宮太子說的那樣?”高允說:“為臣才薄,謬參著作,犯觸天威,罪應滅族,今天已到臨死了,決不敢虛妄。殿下因為臣為他講書時間很長,哀憐為臣,為臣求命。如皇上不問臣子,臣便沒有這番話。既問了,臣如實對答,不敢絲毫迷亂。”魏世祖對恭宗說:“正直,這也是人情所難,而你能臨死不移,這就更難了!而且以實對君,真是忠貞的臣子。像你剛才這一番話,朕寧願漏一有罪的人,也應該寬恕你。”高允竟得免罪。於是召崔浩到皇帝麵前,讓人詰問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應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條有理。當時世祖憤怒至極,命令高允擬詔書,自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滅九族。高允表示懷疑而不擬詔,帝頻頻催辦。高允請求再見一次皇上,然後再擬詔書。帝讓他去了,高允說:“崔浩所犯,如還有別的罪,臣不清楚。如隻是這一項罪行,還不至於被殺。”世祖震怒,下令武士綁了他。恭宗又拜請。世祖說:“如果沒有這人招惹我,就該有數千人死了。”崔浩最終還是被滅了五族,其餘的人都僅以身死。宗欽臨刑時說:“高允大概是聖人吧!”
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複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謁鳳池,仍參麟閣,屍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
恭宗後來責備高允說:“為人應當把握時機,不知見好就收,學識又有什麼益處?在那種時候,我從旁點撥你,你為什麼不順著點,讓皇上那樣動怒。現在我每每想起來,還心有餘悸。”高允說:“為臣本是東野一介平凡書生,本來就無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應朝廷選士之舉,為官鳳池,參撰麟閣,屍素官榮,妨賢已久。大凡史書,都是帝王的實錄,是將來的寶鑒,通過史書,今人可以觀往,後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舉動,無不備載,所以人君應該謹慎從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榮耀當時,他卻辜負聖恩,自招毀滅。就崔浩的行跡,也時有可論之言。崔浩以蓬蒿之才,負朝廷棟梁之托,在朝廷無可稱讚的節操,在私下裏也無可稱道,私欲淹沒了他的公正廉潔,愛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這是崔浩的罪責。至於書寫朝廷起居的事情,說國家得失的事實,這也是史書筆法的大體模式,沒有什麼違背。但為臣與崔浩其實是同參一事,死生榮辱,義無獨顧。能有今天,實在是多虧殿下仁慈廣大,違心苟免,不是為臣當初本意。”恭宗麵容改觀,稱歎不已。高允後來跟人說,我不遵照東宮太子安排的去做,是擔心這樣會辜負翟黑子。
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阝,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雲:‘無邇小人’。孔父有雲: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曆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俊乂不少。頃來侍禦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
恭宗晚期,頗為親近左右侍臣,營立田園,以取其利。高允諫勸說:“天地無私,所以能覆載萬物;王者無私,故能包養眾生。過去的明達王者,以至公之心主宰萬物,所以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以無私之心昭示天下,用至儉之言訓示萬民,所以他們美名盈溢,千載不衰。而今殿下您是國家儲君,四海歸心,您的言行舉動,為萬方所遵,而您卻營立私田,畜養雞犬,甚至販酒市井,與民爭利,天下議論您的聲音四方流布,無法追掩。天下,是殿下的天下,您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能得到,什麼願望不能使人順從,卻與販夫販婦們爭此尺寸之利。過去虢國快亡時,神靈下降,賜予田地,終而喪滅其國。漢代靈帝,不修飾作為人君的持重,喜歡與宮人們一起列市叫賣,私立府藏,以營求小利,終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如此,很可畏懼。大凡作為人君的,必須在擇人問題上十分審慎。故稱知人則聖哲明智,是皇帝難以做到的事。《商書》說“不要親近小人”,孔夫子有言,小人如親近他們便行為不遜,疏遠他們則心懷怨恨。武王愛護周、邵、齊、畢諸公,所以能稱王天下。殷紂溺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失自己的國家。縱觀古今興亡之事,無不由皇帝擇人所決定。而今東宮的確可以說缺人才,但英傑卻並不少。一向以來侍禦在您左右的,恐怕不是將來您在朝的人選。所以臣希望殿下您能稍稍體察為臣愚言,斥出邪佞,親近忠良,所在園田,分給貧苦的人,畜產販賣之類,都要適時收散而去。像這樣的話,則休明的稱讚一天天到來,議論與批評就會逐漸消除。”恭宗沒接受他的意見。
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
恭宗去世,高允久久未能進見。後來魏世祖召見他,高允升階逴欷,悲不能止。魏世祖流著眼淚,命高允退出。左右官員沒人知道其中緣故,議論說:“臣等見高允無由而泣,讓陛下為之悲傷,什麼原因呢?”世祖聽說,召集他們說:“你們不知道高允很悲傷嗎?”左右說:“為臣看到高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傷,所以我們在竊竊議論。”世祖說:“崔浩被誅殺時,高允也應該去死,是東宮苦諫,才免於一死。今天沒有了東宮,高允看見朕因而很悲傷啊。”
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睿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誌》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高允上表說:“往年領詔,令臣收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大致可以閱讀了。臣聽說箕子陳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都是用來彰明後土,景測皇天的東西。所以它們能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福禍,天人的確相去甚遠,但又如聲、響相應,很可畏懼。自古以來的帝王無不尊崇其道而尋其奧妙,以此修正自身。其後的史官都記載了他們的事,以為鑒戒。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到漢代的命運很危險,大權歸於外戚,屢屢陳述妖異之事希望引起重視而不被采納。於是檢索《洪範》、《春秋》中災異報應的人與事而為其作傳,企圖以此感悟其主,但皇帝終於聽不進他的話,終而危亡。這難道不是很悲哀嗎?為臣竊以為陛下神武齊天,睿鑒深遠,欽若稽古,都由舊章,前言往行,無不深究,這是前代皇帝所趕不上的。為臣學識不廣博,識見寡少淺薄,害怕無以拓廣聖德,仰酬皇上明旨。今天謹依《洪範傳》、《天文誌》收集其事實大要,略其文辭,共為八篇。”世祖看了稱讚寫得好,說:“高允對災異的了解,哪比崔浩少?”等到高宗即位,高允出了許多計謀。司徒陸麗等人都受到皇帝重賞,高允既不蒙褒揚,又終身不發一言。他的忠誠而不自矜,大致都如此類。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禦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眾,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
給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機巧,老想呈顯自己的才能,勸高宗大興宮殿。高允勸諫說:“我聽說太祖道武皇帝平定了天下後才開始興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農閑之季,絕不興工。現在建國已經很久了,宮室也已經完備了。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來接受萬國的朝賀,西堂的溫室也可以用來讓聖上休息,紫樓台高可以用來觀望遠近。如果要再修更壯麗的宮室,也應當慢慢地準備,不可急於求成。估計砍材運土以及各種雜役就需兩萬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飯,就合四萬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會挨餓,一婦不織就有人會受凍。何況是數萬之眾無法從事耕織生產,他們所要耗費花銷,實在太多了。往古時推論再來驗證現在,必然有借鑒之效啊,希望皇上認真思考。”高宗接納了他的意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乃諫曰:
高允因高宗繼承太平之業但風俗依舊,婚娶喪葬都不依古製,於是勸諫說: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裏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為政者先自近始。《詩》雲:“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
“前朝的時候,多次頒發命令,禁止婚娶不得作樂以及葬送之日的歌謠、鼓舞、殺牲、燒葬,都在禁令之中。雖然命令頒布很久但風俗仍未改變,大概這是因為處於上位的人不能立即改正,下麵的人也就習以為俗,教化遲慢,已到這種地步。過去周文王靠百裏之地,修德施政先從寡妻開始,再到兄弟,最後到家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聰明的執政者都要先從近處開始。詩經中講:‘你們接受了教化,百姓才會仿效啊。’作為君主,一舉一動,不可以不慎重啊。
《禮》雲: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
禮記中講,嫁女的家裏要三日不滅蠟燭;娶媳婦的人家,三天不進行樂舞。現在各個王室每當娶婦人,都讓樂部派人來舞奏表演,卻惟獨禁止百姓作樂,這是第一個不同啊。
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禦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籓懿。失禮之甚,無複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
古時結婚之人,都選擇德義之門,精心挑選貞潔賢雅的女子,先進行媒聘,繼後送給禮品,會集親友用來表示對別人的尊重,親自駕車用來表示尊敬,婚姻之際,就是如此的困難。現在各個王子年方十五便賜給妻子另起居室,但能配之人,有的年齡過於懸殊,有的出自犯罪之家,用她們來和王子結合,成為其他婦女的表率,這是最大的失禮啊。往年到現在,多有核查彈劾,大概是諸王過於嗜酒而導致詰責,但原因之起,也是因色衰相棄,導致這種糾紛。現在皇子娶妻,多出於宮庭,令天下百姓,必須依照禮法所定,這是第二個不同啊。
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製,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屍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
萬物之生,沒有不死的,古時的聖主明君,定出製度,所以養生送死,見於人情。如果毀生用來奉死,就是聖人所禁止的了。但是葬是藏的意思,死者不可能再見麵了,所以深藏下他們,過去將堯葬於轂,而百姓並不停止在這塊土地上耕種,舜被葬於蒼梧,百姓並不因此不做買賣。秦始皇造地下宮殿,下麵有三條泉水,金銀財寶不可計數,死不多時,就被焚屍掘墓,由此,堯舜勤儉,始皇奢侈,對錯就很顯然了。現在國家營造葬事,費耗巨億,一旦焚亡,全為灰燼,這麼奢侈怎麼有益於死者呢,古時的大臣都不以為然。現在上麵為之忙個不停,而讓下邊百姓必須做到,這是第三個不同啊。
古者祭必立屍,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
古時喪葬必立屍主牌位,按照長幼大小序列,以便讓吊亡者有所憑依來送致祭食品,現在已埋葬的人,人們隻求其相貌類似者敬如父母,美麗的敬如夫妻,敗風傷俗,擾亂情感禮節,是最大之過呀,上麵不禁止,下邊不改正杜絕,這是第四點不同呀。
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汙辱視聽。朝庭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
所以,祭祀是為了確定禮儀,教化天下百姓,所以聖明之君特別重視。到了爵器盈而不飲,菜肴幹了不吃,音樂不是雅聲不奏,物非正色不陳列。現在的大會,內外不分,相互混雜,醉酒喧鬧,沒有儀式,又讓一些戲子表演,汙辱視聽,朝廷以此習俗為美,而責備風俗不清純,這是第五點不同啊。
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厘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現在陛下為王的王,承襲晉末大亂以來的弊俗而不猛烈地糾正改變,來扭正惡習,我擔心天下百姓將永遠不能聽聞禮教了呀。”
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
高允這樣說並非一次,高宗從容聽著他的話,有時即使有衝撞之處或者皇帝不想再聽時,就讓左右將他扶出去。遇有不便當朝說的,高允就請求私下相見。高宗知道高允的意思,把左右摒退後再等待他,對他十分敬重,有時早晨進宮晚上出來,有時幾日在宮裏,朝臣都不知他和皇帝說了什麼。
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麵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麵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征遊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
有的人上書表述這樣做的得失。高宗看後對群臣說:“君父同一啊,父有對錯,兒子為什麼不於眾人之中做書規勸,使他人知道錯而不在家內隱瞞呀。這不是因為是父親,恐怕彰惡於外嘛。現在國家善惡,不能麵陳而上表公開勸阻,這不是故意宣揚君主之錯而表明自己的正確嗎?像高允這樣的人,才是忠臣啊。我有對錯,經常正言麵論,哪怕是我所不願聽的也要侃侃而言,不加避躲。我知道自己的過失而天下不知道他在規勸,這不是忠直嗎。你們在我左右,我不曾聽到一句正論,但伺機見我高興時求官乞職。你們持弓帶刀侍奉我左右,等於是白白站立,卻都做到公、王一職,這個人用筆幫助我匡正錯誤助益國家,官才不過做到一個郎中,你們就不自愧嗎?”於是任命高允為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司徒陸麗說:“高允雖然蒙受恩寵,但家裏貧窮得像普通百姓,妻兒都無以為生。”高宗怒道:“怎麼不早說,現在見我用他,才告訴他的貧困之狀!”這天到了高允家中,隻有草屋幾間,布被麻袍,廚房中隻有一點鹽菜。高宗歎息說:“古時的人有清貧到這樣的嗎?”立即賜給綿帛五百匹,糧食一千斛,拜高允長子高忱為綏遠將軍、長樂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堅決推辭,高宗不答應。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遊雅等大多已經官至侯爵了,以及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為郎中二十七年沒有升過官,當時百官沒有俸祿,高允常讓自己的幾個兒子砍柴采果來自己供養自己。
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湣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複以本官領秘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
開始,尚書竇瑾因事被殺,其子竇遵逃到山穀之中,其母焦氏被收進縣官衙門,後因焦氏年老而得免受辱。竇瑾的親朋故舊中沒有敢資助的人。高允可憐焦氏年老,將其留在家予以保護,六年後,竇遵才得到恩赦。高允的品行大都如此。後轉為太常卿,本來的職責仍同過去一樣。高允上《代都賦》,來規勸皇上,也與《二京賦》相似。因文字太多,本書就不記載了。當時中書博士索敞和侍郎傅默、梁祚論辯名字的貴賤,議論紛紛,高允於是撰《名字論》來解釋其迷惑,有許多考證。後來又以本官領秘書監,解除太常卿之職,晉爵為梁誠侯,加左將軍。
初,允與遊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嚐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餘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嚐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餘常呼為‘文子’。崔公謂餘雲:‘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餘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崇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崇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嚐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
最初,高允同遊雅以及太原張偉同業友好,遊雅曾評論高允說:“大概喜怒是一生所不可能沒有的。但以前史書記載卓公為人寬厚持中,文饒度量宏大,偏心的人有的不相信。我和高允相處四十多年了,沒有見到他有喜怒之色,不得不相信了呀。高允內文明而外柔弱,說話呐呐似乎不能出口,我常叫他‘文子’。崔公對我說:‘高允才大學博,是一代名士,所缺乏的是一種矯直剛昂的風節啊。’我認為有道理。司徒被處罰,起因是很小的錯失,卻受到了皇帝下令斥責,崔公聲啞股戰而不能說話,宗飲以下更是伏地流汗,麵無人色。惟獨高允陳述事理,解釋是非,辭又清辯,聲音洪亮,明主為此而動容,聽者無不予以稱讚。仁義惠到同僚親友,因此而能保住身家。向來所謂正直的人,更能做到這樣嗎?宗愛他有勢力的時候,威名振於四海,曾經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人都望庭中相拜,獨有高允是到階前長揖,由此可以看到,汲長孺可以躺著見衛青,這怎麼能說是抗禮呢?向來所謂風節的人,能夠這麼稱讚他們嗎?知人固然很不容易,但人也不易知道自己,我既然失之在內心,崔浩也外顯漏於形體。鍾期隻限於聽伯牙之奏樂,管仲也隻有鮑叔最能明其心跡,很少有人能夠這樣啊。”高允的為人被當時人推崇如此。
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恆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暗,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後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為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複見於今。朕既篡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鹹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複。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鹹寧,百揆時敘。申祖宗之遺誌,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鬱鬱之音,流聞於四海。請製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高宗敬重高允,通常不呼他的名字,習慣稱之為“令公”。於是“令公”之號傳遍四方。高宗去世,顯祖居位時還很幼小不能承擔大業,乙渾專權,圖謀危及國家,文明太後殺了他,召高允到禁宮中參與謀斷大事,又下詔給高允說:“很久以來,學校不建,為日已久,道肆陵遲,學業荒廢,學子憂歎,又見於今。朕繼承大位八方安寧,查考舊章,想設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能有所寄托。你為儒宗元老,朝庭內外德名遠揚,應當同中書、秘書二省官員共同參商後奏報。”高允上表說:“我聽說經綸大業,必須以教養為先導,規範九州也要靠文德來輔其成功。所以要在祭禮後出奏《周頌》,讓《魯頌》在宴廳上播揚,但從永嘉以來,舊的規章沒有了,鄉間再無雅頌的聲樂,城市杜絕了隆重典禮的製度,道業中斷近一百五十年。仰想先朝曾準備恢複規章製度,發揚聖賢的思想風尚,因為正值多事之時,未能最終完成。陛下敬重文明,繼承大業,萬國安寧,風調雨順,申明祖宗的遺誌,興盛周禮的絕業,發布德音,振興文教,士民百姓,都深感為幸。我承受詔命,並會同中書、秘書二省披閱史書,準備製定規章製度,怎麼能不敦促儒者去從事教育之業,敬重學習以堅定這個道理呢。此詔大義,實與古義相通,當秉遵聖旨,興建學校以正風俗,使先民之道再現於今日;讀書之音,流傳在四海。請求規定每大郡設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收學生一百人;其餘的郡府,立博士二人,助數二人,收學生六十人,最次的郡府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收學生四十人。博士應是博通各種經典,世代忠貞清白能為人師的人,年齡當在四十以上。助教選拔也和博士同,年齡限在三十歲以上。如果學業早已有成,有才能任教授者,就不限年齡,學生要收郡府中品行清廉,素有名望,可以遵循名數的人,先從高門望族中挑選,再往下延推至其他人家。”顯祖聽從了他的意見。郡府成立學校,就是從此開始的。
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征,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征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群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於下:
後來高允因年老多病,屢次上書請求告老還鄉。皇帝不許,於是寫下告老詩,又因過去一同共事之人已零落將盡,感懷故去之人,做《征士頌》,大約限於應命的人,如果有征召命令而沒到者,則付諸缺如。群賢之行,敘述主要梗概。現列於下麵:
中書侍郎、固安伯範陽盧玄子真
“中書侍郎、固安伯範陽人盧玄,字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郡功曹史博陵人崔綽,字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燕崇玄略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人燕崇,字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人常陟,字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獻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人高毗,字子商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人許堪,字祖根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人杜銓,字士衡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人書韋閬,字友規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人李詵,字令孫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钜鹿公趙郡人李靈,字虎符
太常博士、钜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人李遐,字仲熙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人張偉,字仲業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傳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範陽人祖邁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範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範陽人祖侃,字士倫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範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縣子中山人劉策
東郡太守、蒲縣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人許深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人宋宣,字道茂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人劉遐,字彥鑒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人邢穎,字宗敬
中書郎、武恆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人高濟,字叔民
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人李熙,字士元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李熙士元
秘書監、梁郡公廣平人遊雅,字伯度
秘書監、梁郡公廣平遊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人崔建,字興祖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人宋..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人潘元符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人杜熙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人張綱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穀人張誕,字叔術
中書郎上穀張誕叔術
秘書郎雁門人王道雅
秘書郎雁門王道雅
秘書郎雁門人閔弼
秘書郎雁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人郎苗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穀人侯辯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穀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人,品秀才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大概諸王的禦士之道,沒有不是憑著收伏群才,用來興隆治道的,所以周文王以擁有眾多士人安定天下,漢武帝以得到賢才成就一代盛世。這些都記載於史書之中,是自古的恒常之理。魏自神慶以來,天下平定,誅殺赫連幾世竊據之勢,橫掃蕩平不服順的敵寇,南邊平定江楚一帶,西邊掃蕩涼城之地,很遠的地方都仰慕而來,於是休兵息甲,修立文學,延攬賢才,谘詢政事。夢想賢哲,想遇這種人物,詢訪各有關部門,來訪求有名之士。都稱範陽盧玄等四十二人,是士冠之裔,各個州縣都有名聲,可以作為羽翼之用。皇帝立即親自發布命令,征召盧玄等人。於是留著官位等待,空著爵位準備分封,真正來應命就征的有三十五人,其他按慣例於各州郡所派選之人不可勝數。於是英士滿朝,濟濟一堂而為一時之美。過去我和他們都蒙抬舉,有時從容於廊廟,有時遊宴在私門,上讀公務,下盡歡娛,認為千載一時之聚,從此開始。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時受征之人,大都零落將盡。在的隻有幾個,也都分於各處,過去的快樂變為悲涼之歎。張仲業東臨營州,遲遲不能返還,一同相敘,共憐惜於垂暮之年,述情於夕陽將落之際。這個人不幸又突然故去。在朝中的都是後進的學子,與我傍居的也不再是舊日之人。進入沒有交心的地方,出入沒有表誌的地方。自己反省自己,所以感慨不已,大概稱頌的人讚美盛德的形容,也可以用來做長言來寄托我對他們的思念。不做文已二十年了,但是事情記於心中,怎麼可以埋沒呢?於是寫作頌詞說:
夫百王之禦士也,莫不資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發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蕩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俊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鹹稱範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征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征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複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於懷,齊衿於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複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裏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為之頌,詞曰:
紫氣幹宵,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東屢駕,掃蕩遊氛,克剪驕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數無外,既寧且一,偃武..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岩隱投竿,異人並出。
紫氣幹霄,群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蕩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岩隱投竿,異人並出。
....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陣,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
亹癖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
茂祖煢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茂祖煢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燕、常篤信,自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棲遲。居衝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棲遲。居衝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
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
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
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思,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群後。
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群後。
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
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
卓矣友規,稟茲淑亮,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
卓矣友規,稟茲淑亮,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
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以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
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夭,跡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
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夭,跡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
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眾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
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值艱難,常一其操,納眾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
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誌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
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誌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
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
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聘說,入獻其功。..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翰飛紫冥。頻在省闥,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恥於下,乃謝朱門,歸跡林野。
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恥於下,乃謝朱門,歸跡林野。
宗敬延譽,號為四俊,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彖,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
宗敬延譽,號為四駿,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蠿,賦德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
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
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
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遊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逾群。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孔稱遊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逾群。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
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
潘符扌票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
潘符詄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
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鬥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不係心,得不形色。
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鬥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不係心,得不形色。
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
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治。性協於時,情敏於高。與今而同,與古曷異。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文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
季才之性,柔而執競,郕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
秀才之性,柔而執競,屆陂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
群賢遭世,顯名有代,誌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舉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漼爾增哀。
群賢遭世,顯名有代,誌竭其忠,才盡其概。禮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舉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忻如昨,存亡奄乘。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誛爾增哀。
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番,往因時囗,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裏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剪厥旅,積骸填穀,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窮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屍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曆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
皇興年間,皇帝下詔讓高允兼任太常,到兗州祭祀孔子廟,對高允說:“這次檢閱德行的行動不要推辭了。”後來高允跟隨顯祖北伐,大勝而歸,到武川鎮時,奏上《北伐頌》,文中寫道:“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囗,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陣,馘翦厥旅,積骸填穀,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窮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屍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曆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後